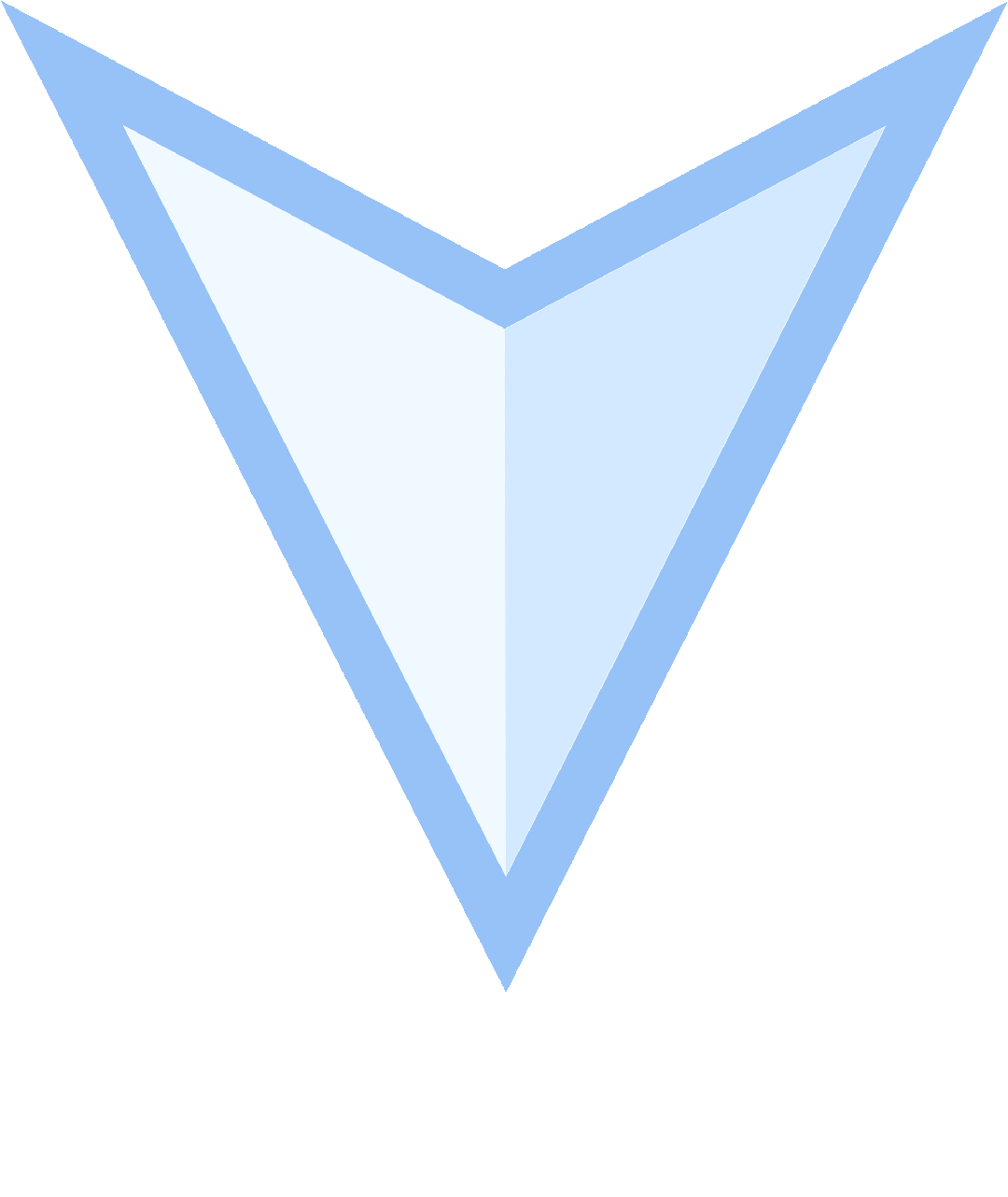1945年8月15日,同济青年广播新闻社用自制的无线电将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李庄:
抗战胜利了!小日本投降了!
那天晚上,吴孟超喝醉了。
李庄沸腾了,同学们纷纷上街狂欢,茶馆饭店街上到处都是人!富裕一点的同学倾其所有,领着大家上了当地最高级的“留芬”饭店吃饭喝酒。
在北碚,复旦的学子闻讯后都兴奋地跳起来,甚至砸碎了好多茶馆的茶碗。登辉堂前立刻悬挂出了两只汽灯。夏坝上的爆竹声,相连不断响彻云霄。校长亲自提了火把,领导学生唱抗敌救亡歌曲。第二天,几个院长都上台唱了戏,陈望道先生因为不会唱戏,在同学们再三催促中,诵读古文一篇,甚为精彩。同学们欢呼不已。
今日,我们沿着江水,从长江第一古镇李庄,一直来到重庆北碚的作孚广场。夜晚,人们在江边散步,几个孩子在嬉戏,小贩在卖凉粉。有人开了直播,对着支起的手机唱歌。夜晚的江面上没有灯,但能依稀看到湍急的河水拍打着两岸。几个年轻人趴在江边的栏杆上,不疾不徐地聊着天。不再有恐惧,不再有痛苦,不再有破碎,这是和平年代一个平常的夜晚,却是当年众人从未奢望的宁静。
1944年,在李庄的同济学生响应“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万青年十万军”的号召,全校1/3的学生近700人报名参军,其中不乏家境优渥的子弟,有近视的学生为了通过视力检测,硬生生背下了视力表。1945年1月4日,在江边的北碚轮船码头,复旦师生高举“欢送江汉健儿”欢送从军同学。那一刻,“祈战死”的歌声直冲云霄,那一刻,学子们都愿意奔赴未知的战场以身许国。
炮火的凶残,无法改变河流的方向。
属于正义的胜利,终于到来!
1945年12月,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决定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进行审判。42岁的复旦大学教授梅汝璈被选为中国法官。1946年3月19日,梅教授从上海启程赴日。也正是在1946年9月底,最后一批复旦大学物资、员工和行李乘船东下,复旦大学留渝迁校办事处完成使命解散。
在李庄,当满载着学生老师和书籍的船身,远到再也看不见时,古镇又恢复了静谧。
但有一些东西留下了。师生们帮助古镇比县城更早10年用上电灯,举办的“人体解剖展览”给古镇带来了科普启蒙。正是因为李庄在川,1946年初,吴孟超医前期考试通过后,到四川宜宾(当时医学院设在宜宾)进入医后期学习。新中国成立后,这一时期同济毕业生中成为“两院院士”的就有20余位,包括朱洪元、陶亨咸、唐有祺、俞鸿儒、卢佩璋、吴孟超、王守武、王守觉等人。
复旦则在夏坝原址留下了私立相辉学院(后被并入西南农业大学、重庆财经大学等),许多制度均延续了复旦作风。1949年,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考入该院农学院。
大学之大,非有大楼之谓也,乃有大师之谓也。
这句话的含金量,随着时间的推移,越发显出珍贵。一如江水啊,什么都记得。
今年出版的《中国抗战》记录着: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,全民族抗战爆发前,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共108所。八一三事变后,上海的同济大学、大夏大学、复旦大学、光华大学、上海法学院、东吴大学、吴淞商船专科学校、私立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等8所院校相继内迁。除了大夏大学迁贵阳和赤水外,其余均辗转奔向四川。
这一次高校内迁至大后方,是在炮火中的无奈之举,但师生们却用人格竖起了精神的丰碑,支持了抗战,也赓续了教育,并在多方面推动了西南地区教育现代化,为中华民族保留了科学和文化的种子。
书中写道,那个时代,“校园墙内浓厚的民主气氛,感染着围墙外的广阔世界,甚至辐射到穷乡僻壤,而且内迁高校师生通过教学科研活动,与工矿业企业专业技术人才结合,为战时生产与科研做出了巨大贡献。”
文章来源于:http://www.ljyz.org.cn 一中学网
网站内容来源于网络,其真实性与本站无关,请网友慎重判断